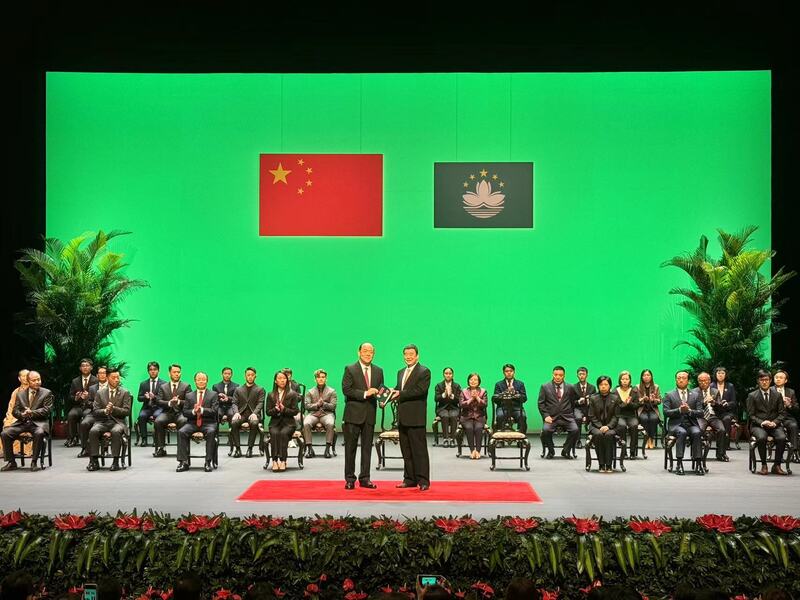當“一帶一路”遇到國家安全
“一帶一路”旨在推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和更深層次的資源優化配置,但它實際上面臨着更多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包括了“一帶一路”涉及的多個國家在內的政局不穩、恐怖主義、經濟制裁、地理限制及收入差距等不穩所造成的衝擊。“一帶一路”共涉及60多個國家,總人口達44億,GDP約21兆美元,分別佔世界的62%和29%。沿線國家是傳統地緣政治和民族、宗敎、文化、制度等衆多矛盾盤根錯節的地區,也是當今世界安全問題最為嚴重的地區。
推動“一帶一路”將各國與中國推進到一個相互依賴的國際網絡之中,國家安全將被納入開放的國際安全體系之中。國家安全的威脅往往是受制於特定的社會環境條件,是越來越具有不確定性的一面。從中國收購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口(Gwadar Port)、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Colombo Port)等重要基礎設施涉及到安全因素,是引發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質疑。美國與印度政府都質疑中國在印度洋展開的一系列活動,意圖在印度洋發揮中國的影響力。外界一直傳聞中國再次在“一帶一路”中有意在泰國的克拉地峽(Kra Isthmus)建鑿運河溝通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構想。這必然引起更多馬六甲海峽周邊國家的反對,尤其是中國在東南亞重要的戰略夥伴國家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印尼。藉由克拉地峽的開鑿可能為中國解決“海上生命線”的部分問題,但衍生更多的非傳統安全議題有待解決,更以周邊國家的外交制肘至為嚴重。
從“一帶一路”援助與投資標的中,以交通、電信、能源涉及到國家安全的考量引起關注,包括國土安全及經濟安全。這兩個安全範疇往往受到政治與法律問題的挑戰,尤其是經濟安全帶來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即一般國家面臨“一帶一路”創造的經濟效果的同時,亦面臨經濟效果背後意涵的政治因素,包括跨境合作產生的主權問題、經濟依賴度及外交威嚇等手段。傳統的安全不僅體現在主權安全,還包括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環境安全和資訊安全等更為廣泛的內涵。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港口、建高鐵、買油田、蓋水電站,已引起不少國家擔心中國如此過度投入“國家安全產業”而構成國安問題。由於“一帶一路”實施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周期長、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有關合作國家的政策政治穩定和對華關係狀況。二者之間的矛盾增加了“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政治風險。一些區域國家的政治勢力基於利益及安全困境兩大關鍵考量下,將採取多元的競合策略,即在合作基礎上展開競爭。早期的“中國威脅論”或”紅色資本”帶來的威脅將給“一帶一路”更多的阻擾,進而使得中國得付出更多的“代價”換取他國的“談判價碼”。
“一帶一路”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風險,最大的風險是中國的重商主義和各國民族主義、大國地緣政治勢力三股力量的交鋒衝突。很多專家指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經常發生良莠不齊的投資也會發生。其次,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量多而繁雜,周邊國家政局動盪,政權輪替或政變都有可能導致各種早前的投資承諾取消或重啟。加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機制不成熟、政治和社會不穩定性風險較高、勞動力成本較高或勞動力素質較低,以及部分國家經濟發展形勢不佳、國內市場空間相對較小,限制了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的投資。
在“一路”的多國之中,馬來西亞與印尼扮演的地緣角色或經濟效能都是關鍵的。馬、印兩國都位處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重要通道的馬六甲海峽,是中國國家利益的所在,也是世界樞紐的關鍵扼喉。印尼是東盟非常重要的大國,馬來西亞是最早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積極拉攏馬、印兩國都有深層次的戰略意義,特別是印尼對基礎設施有一定的需求。中馬經貿往來密切,二○一三年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馬來西亞於二○一五年接任東盟輪値主席國,有助於為中國——東盟關係鋪設良好的溝通平台,同時可在爭議的“南海問題”上紓緩緊張的外交氣氛。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馬兩國可在物流、資金流、經驗交流及人流方面重點着手深化合作,鼓勵中資企業以低貸款利率(給馬來西亞的州政府)、低成本優勢投入馬來西亞的基礎建設工程,包括港口建設、公路系統及大橋建設。在銜接新加坡和吉隆坡的新馬高鐵工程上,中資與日資承包商在其中的競標也成為“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區域的另一角力亮點。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海洋大國,也是東南亞最大的國家,更是區域政治經濟的關鍵國家。地緣政治使得中美等西方大國紛紛向印尼伸出“友誼之手”,對地區穩定與政經發展都極具戰略角色。在經濟方面,印尼除了擁有2億人口的市場外,同樣也是世界主要的能源出口國。尤其是透過中國的投資商在“一帶一路”下,合作提高印尼能源產量並引導其出口,並在發電厰設備和技術方面協助印尼發展電厰,保證印尼的各個島嶼獲得充足的能源供應。另外,由於印尼在運輸高度依賴海運的基礎設施,發展長期滯後,內海航運業具有發展潛力和可觀的經濟利益,對中國造船業帶來很大的良機。
綜合上述國家安全議題與戰略風險,中國政府有必要增進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基本國情、價値觀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的了解認知。同時,在國家發展道路與國內民族主義取得平衡,避免引起他國的擔憂,務實強化“一帶一路”在國際社會的認同,並透過人文互動擴大國際間的互信基礎。這將使中國在地緣戰略上銜接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海權延伸戰略得以佈局與發展,具體深化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地緣關係,由根本上解決圍繞的多國關注的國家利益問題。最終,如何在顧及各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安全的前提下,妥善發展“一帶一路”的戰略效果,就視乎中國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協調能力,以及外交操作的技術含量。
政策載具:亞投行眞的行嗎?
亞投行是中國對“一帶一路”融資政策的載具。二○一五年四月十五日,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有57個,其中域內國家37個、域外國家20個。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為支撑中國“一帶一路”策略提供融資,為的是要建立以中國為主導的新歐亞聯盟。從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融資性質來看,國家開發銀行、國家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起着主導作用,也擔負着更大的責任。
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二○一○至二○二○年,亞洲各經濟體的基礎設施要想達到世界平均水準,需投入8兆美元,融資需求和融資缺口巨大。“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可以滿足沿線國家改善基礎設施的資金需求。在另一邊廂,自一九六六年就開始深耕亞太區域國際金融借貸機構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亞銀)正面臨亞投行的挑戰。冷戰末期至今,亞銀順應時勢發展成亞太區域整合的重要融資機構,主要協助區域國家在基礎建設的融資與國家融資。亞洲地區的基礎建設需求龐大,亞銀預估每年高達7,500億美元。亞銀的經濟學家表示,亞銀二○一四年在亞洲的貸款總額只有220億美元,遠低於亞洲地區的開發需求。據亞銀估算,從現在到二○二○年,亞洲地區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到7,300億美元,現有的世銀、亞銀等國際多邊機構都沒有辦法滿足這個資金需求。相較亞投行與亞銀,在宗旨、運作機制、資金規模、治理經驗及領導決策等方面都有所差異(見附表)。
整體而言,無論在治理經驗、運作機制及資金規模上,亞投行仍與亞銀有一段明顯的差距。値得注意的是國際秩序已仰賴美日主導的“體制”,雖然亞投行可彌補中國及小國在區域金融秩序的話語權,但亞投行在國際政治現實與經驗仍不足以與亞銀正面競爭。亞銀在戰後數十年的國際投行運作經驗及其運行機制,實際上已經形成美日主導體系與亞太區域國家的合作關係,非亞投行在短時間內能夠融會貫通。概言之,目前的亞投行是足以作為“一帶一路”的政策金融載具,但因亞投行在治理經驗與更多的地緣考量因素而將成為日後運作的挑戰與障礙。中國大陸將美國的TPP與“重返亞洲”政策,視為圍堵中國的“政治手段”。目前日本與美國在該區域擁有一定政治與經濟勢力。因此中國大陸是以“削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勢力”為總體戰略目標,以對抗及圍堵的策略,回應美國的亞太政策。若然,在“零和遊戲”(Zero-sum Game)的條件下,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以“發展中國家”仍難以對抗美日主導的亞銀或世銀,實際上也加劇“發展中國家集團”與“已開發國家集團”在區域金融秩序的競爭。
(資料來源︰澳門日報 2015/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