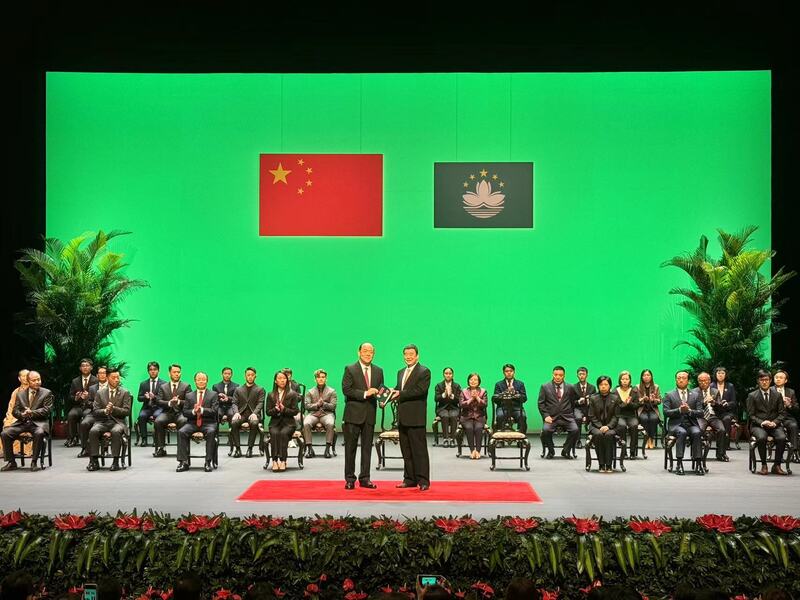摘 要:“一国两制”下,中央拥有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同时授权特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既是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央行使主权的应有之义。同时,中央的全面管治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是辩证统一的。中央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是中央对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中央不主动干预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另一方面,高度自治权不能没有限度,中央对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有监督的权力。
关键词:主权 授权 全面管治 高度自治
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首次提出全面管治权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新时代“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成为新时期中央治国理政、有效管治香港特区的崭新课题。根据“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中央人民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同时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虽然通过授权理论,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疏通了“一国两制”下中央管治与特区高度自治的关系,但实践中的问题要更为复杂。尤其是全面管治权的法理依据,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关系,全面管治权的内涵与范围等问题,均在社会中引起一定的争论,有必要对相关概念予以界定,厘清全面管治权与主权、治权、高度自治权之间的逻辑关系,明晰全面管治权的具体内容,准确理解和实施基本法。
一、“一国两制”的不同言说方式:全面管治权的提出及其必要性
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单一制国家的大框架内,“一国两制”理论成功解决了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和澳门的统一问题。“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有目共睹,充分体现了当代国人的政治智慧与实践能力。但是,“‘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1]随着两个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同时,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深化“一国两制”理论的科学内涵,以回应现实的挑战。
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对于“一国两制”就有权威的解释,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2]“一国两制”的提出,是为了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认为,香港繁荣的原因不在于英国人的统治,而在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也为了消除港人对未来的不安情绪,对于“一国两制”的阐述更多地集中在“两制”上。在过渡时期,江泽民曾在同香港许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谈话中引用“井水不犯河水”的谚语。[3]此阶段,“一国两制”主要解决的是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问题,我们始终相信,“香港人是完全能够治理好香港的。”
然而,从香港回归的历史经验来看,香港在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富分化、“港独”思潮等“高度自治”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国”与“两制”、“两制”之间的内在张力逐渐显现,“这就意味着中央不得不放弃‘统而不治’的想法,探索在行政主导体制下如何治理香港”[4],思考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更加强调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两制”的前提,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5]以2003年为分水岭,中央治港政策开始由“消极不干预”向“不干预,有所为”转变,强调香港与内地是命运共同体,“祖国内地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香港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
随着以“普选”为议题的政治争拗愈演愈烈,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受阻又反过来加剧了社会的进一步撕裂。尤其是近几年来,香港社会乱象丛生,香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不增反减,文化鸿沟日益加深,从“占领中环”到“旺角暴乱”,从立法会频繁“拉布”到立法会议员辱国“宣誓风波”,香港社会陷入本土意识抬头、社会极端势力膨胀、“港独”思潮泛滥的恶劣局面。“行政主导”体制运行不畅,政府管治效率低下,亟需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力量来解决香港的种种管治乱象。在此背景下,全面管治权的概念应运而生,其提出正当其时。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安全,维护中央依法享有的权力与保障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始终聚焦发展。“作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与之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体制得以确立。”[7]
自1984年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方针科学内涵进行界界定以来的30余年里,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对“一国两制”内涵的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实质都是一脉相承的。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始终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目标,以往更多地强调“两制”,并不代表“一国”不重要,更加不代表中央完全不干预特区的治理,正如邓小平所言,“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8]“港人治港”的确切含义是“港人港官”,即:不让外国人担任特区政府的主要公职,也不让内地人担任特区政府的任何公职。“不要把‘港人治港’误解为只有港人才能管治香港,而中央政府不能管治香港。”[9]因此,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概念,而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要求,符合“一国两制”的精神实质,符合特别行政区治理的现实需要。“全面落实中央管治权是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10]
二、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法理依据
我国两部基本法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同时根据我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特别行政区,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试行高度自治。然而,既然是恢复行使主权,为什么特区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却享有立法权、终审权、独立的财税制度等具有主权性质的本应由中央统一行使的权力?行使主权的方式有哪些?恢复行使主权与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管治权与自治权之间有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将有利于我们分析全面管治权的法理依据,解决现存的一些分歧与争议。
(一)主权的概念及主权的行使
“在国际法上没有比‘主权’更令人困惑的概念。”[11]16世纪,法国的博丹对主权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将主权定义为“共同体所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力”[12]。博丹的主权理论是与封建王权结合起来的,意在巩固和加强王权。后来,君主主权论与洛克、马伯利、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相结合,国王的主权被国家主权替代。“除了少数的例外,19世纪的几乎所有阶级和正当都把国家主权作为一项宗教信条而接受下来。”[13]虽然后来由于与分权主义、联邦主义这两个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不相容而甚至有学者认为“主权理论已经破产”[14]。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但“国家主权是一种不容否定的客观存在”,各国“在现实中都将主权视为国家生命的脊柱”。[15]美国联邦和地方都充分拥有最高权力的观点很快被打破,主权的不可分性与绝对性依然得到强调。[16]
《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认为:“主权是最高权威”[17];《牛津法律大辞典》对主权的定义是:“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概念”。周鲠生先生明确指出:“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18]王铁崖教授认为,“主权,即国家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是国家固有的在国内的最高权力和在国际上的独立权力。”[19]学者们对主权的定义及时没有根本区别,主权有身份及权力两方面的属性,在国际上被用来概括国家的一种地位,对内表现为一国所固有的最高权力。就其内容来讲,主要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在对外方面,主要是外交、国防、领土、宣战、媾和等权力,在对内方面,主要表现在一国领土内的最高统治权。[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表明中国的主权属于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主权。
(二)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是行使主权的应有之义
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学研究和分析的重要课题,[21]自中英谈判中撒切尔夫人在中英谈判中提出“主权换治权”后,尤其是在两岸关系上,台湾当局于1992年单方面提出主权与治权二分主张,关于主权与治权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
治权是“主权的行使方式,从属于主权,是管辖和治理社会的权力”[22]。主权与治权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具有处理国内事务的最高权力,如果主权与治权分开,意味着国家的主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概念,而不能实际行使权力。丧失了治权,主权将成为一句空话。从词义上解释,管治具有管辖和治理的含义,“管治权就是一个国家基于主权而对其所属领土行使管辖和治理的权力。”[23]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即中央行使主权权力。
“特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尊重和维护中央国家主权。”[24] 我国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是指“我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开始行使绝对的和最高的权力”[25],即中央对特区恢复行使的是包括管治权在内的完整主权。因此,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是行使主权的应有之义。
(三)管治权与自治权的关系:关于治权的模糊话语
《白皮书》发布之后,香港社会也产生了一些分歧,有观点认为,香港的高度自治“实质就是管理权也就是治权在香港”,或者认为香港拥有独立治权,“主权不可干预治权”。[26]这是对“一国两制”原则与基本法的误解。全国人大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这种自治权不是主权意义上的治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27]《香港基本法》第2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而非其本身所固有。香港无权制定自己的宪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基本法就是中央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法案”[28]。香港特区在中央的授权下实行与我国其他地方不一致的社会制度,但这“并不说明我国不再属于单一制或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已经改变”[29]。因此,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没有主权属性。
在单一制国家,主权在中央,中央的权力是本源性、全面性的,地方没有任何固有的权力,地方的权力来自中央的授权,并且这种授权也仅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30]人民作为主权者,通过行使主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国家以及全国各地方行使的领土管辖权和统治(治理)权。[31]通过全面管治权概念,中央与特区关系形成“主权——主权的行使(即全面管治权)——全面管治权的行使(包括授权)——高度自治权”的逻辑链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处于国家的完全主权之下。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32]
因此,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不具有主权属性,不应被视为国家管治(治)权,其实质应被视为国家授予特别行政区的、较全国其他地方而言所拥有的程度较广、范围较多的对地方性事务的处理权。[33]“以治权代替高度自治,实际上是为了含糊治权的归属。”[34]
三、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规范基础
虽然宪法与基本法没有出现全面管治权的概念,但基本法的多处规定表明了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中央对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第一,《中英联合声明》及《中葡联合声明》为中央对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提供国际条约上的依据。《中英联合声明》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第2条规定,联合王国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同样的,《中葡联合声明》也明确规定,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两个声明是英国、葡萄牙分别与中国签订的,英国、葡萄牙是“还权于中”,而非“还权于港”、“还权于澳”。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港澳恢复行使包括管治权在内的完整主权。
第二,我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为特别行政区的设立提供了宪法依据,规定了中央的特别行政区创设权。特别行政区是国家决定设立的,实行的制度由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与中央对特区的管治权都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央依法行使宪制权力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重要内涵。”[35]
第三,基本法规定了中央对特区享有全面管治权。两部基本法均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来源于全国人大授权(第2条),充分说明“特别行政区没有固有的权力,其一切权力都是中央授予的”[36]。基本法还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的性质和地位,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第12条);此外,与主权密切相关的重大权力,基本法均规定由中央直接行使,还分别设置了对特区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的监督机制。可以说,中央对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相结合的原则与精神是贯穿于整部基本法之中的。
四、全面管治权的具体内容
全面管治权不是一项具体的职权,而是对国家权力的概括表达,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括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特别行政区自行管理地方事务。
(一)中央直接行使管治权
国家权力事务的范围有纯主权的事务、可授权地方行使的自治事务和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37]中央授权特别行政区行使比一般地方行政区域甚至比联邦制国家下各邦还要多的高度自治权,但宪法和基本法也明确规定了有些权力由中央直接行使。主要包括:决定设立特别行政区和以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管理与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管理特别行政区的防务;任命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者进入紧急状态;批准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改;制定、修改和解释基本法;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协议是否适用于特区。
(二)授权与收回授权
考虑到两地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为了保持香港、澳门特区的繁荣稳定,根据“一国两制”原则,中央授予特区广泛的地方事务管理权,甚至有一些不属于地方性事务的权力也特别授权行政区行使,包括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与各国或各地区缔结互免签证协议等。
除了授权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收回授权也是全面管治权的行使方式。授权不代表授权者丧失其拥有的权力,但基于“一国两制”的原则要求,中央并不干预香港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这是中央对其权力的自我限制,并通过宪制性法律固定下来。“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权力行使的基本界限,即中央的权力不超越自治权的界限,不干预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事务。在法理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自我限制权力的法律标志。”[38]因此,有权收回对特区的授权。同时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也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在此基础上,中央收回授权或者直接行使已经授予特区的权力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而不能随意收回。
(三)对特区高度自治的监督权
“根据授权的法律关系,中央授权香港和澳门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不仅可以设定授权的条件,而且可以监督被授权者运用授权的整个过程,并纠正违反授权的不当行为。”[39]“在授权的概念下,权力主体对被授权者是否按照授权的规定行使其权力有监督权。”[40]因此,对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的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在中央的监督下实行高度自治,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不是高度自治,而是独立自主了。”[41]
基本法主要设置了三种机制来监督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包括对特区立法的备案审查制度,对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以及对基本法的解释权。从具体内容来看,两部基本法中的多项具体规定直接体现了中央对特区的监督权,例如《香港基本法》中第12条规定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第15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主要官员;第43条规定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第17条规定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90条规定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职,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註釋︰
[1] 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宪政法律文献汇编》,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0年版,第260页。
[2]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3] 参见江泽民:《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港澳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4] 强世功:《中央治卷须认真面对“高度自治难题”》,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5] 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港澳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6] 吴邦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港澳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8] 邓小平:《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9] 郝铁川:《论中央对香港的宪制性管治权》,载《江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10] 饶戈平:《“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的启示》,在《中国人大》2017年7月5日。
[11] Morton A. Kaplan and Nicholas B. Katzenbach,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1961p.135.
[12] [法]让·博丹:《主权论》,[美]朱利安·H. 富兰克林编,李卫海、钱俊文译,邱晓磊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3] [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1页。
[14] [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6页。
[15] 杨泽伟:《主权论——国际法商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版,第266-267页。
[16] 参见[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185页。
[17] [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18] 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5页。
[19]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20] 肖蔚云主编:《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21] 王邦佐、王沪宁:《从“一国两制”看主权与治权的关系》,载《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2期。
[22] 董立坤:《中央管治权与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23] 王禹:《“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载《港澳研究》2016年第2期。。
[24] 郝铁川:《香港回归20年来的法治进步、不足和展望——从若干司法判决看香港法治生态发展》,载《江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25] 王禹:《论恢复行使主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26] 摘录自梅丽:《主权治权分割制,高度自治确保行》,载香港《信报》,https://forum.hkej.com/node/ 127641,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13日。
[27] 肖蔚云主编:《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有关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曾引起较大争论。主要观点有:(1)“带有联邦制特点说”,认为香港特区同中央的关系已经超出单一制的范畴,而带有联邦制的特点;(2)“对等地位说”,认为中央人民政府只有在外交和国防事务方面才负起中央政府的职能,在其他事务上应该同香港特区政府处于对等地位,中央人民政府对特区内部事务完全不能干预;(3)“零总和分配规律说”,认为权力的总和是有一定限量的,一方多了,另一方必然少了,中央人民政府应当将所有能下放的权力授予特区;(4)“剩余权力说”,认为除了国防和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其他一切权力属于特区政府。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咨询报告(2)》,第24-29页。转引自许崇德主编:《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8页。
[28] 董立坤:《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法律的冲突与协调》,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9] 王禹:《“一国两制”宪法精神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30] 王禹:《论恢复行使主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31] 蒋朝阳:《国家管治权及其在特别行政区的实现》,载《港澳研究》2017年第2期。
[32] 吴邦国:《深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伟大实践向前推进——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港澳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33] 蒋朝阳:《国家管治权及其在特别行政区的实现》,载《港澳研究》2017年第2期。
[34] 董立坤:《中央管治权与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35] 乔晓阳:《中央对香港具有宪制权力及其实践》,载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央有关部门发言人及负责人关于基本法问题的谈话和演讲》,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36] 董立坤:《中央管治权与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37] 杜承铭:《论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性地方自治性质及其授权机理》,载《暨南学报》2015年第6期。
[38] 肖蔚云主编:《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
[39] 许昌:《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直接行使的权力的分类研究》,载《港澳研究》2016年第3期。
[40] 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41] 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