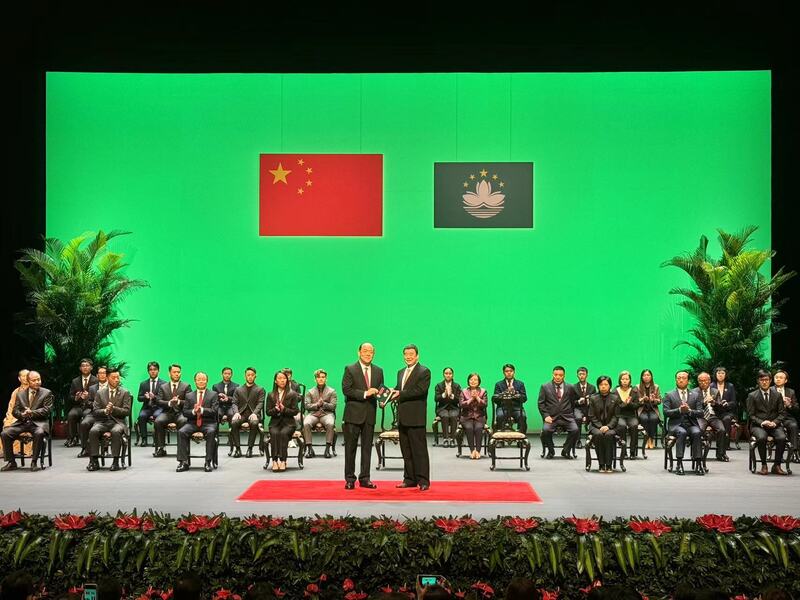香港功能代表制,是一項有一定特色的選舉制度,其特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從港英時期弱勢立法政策協商或者諮詢功能轉而成為一個憲制原則,或者說正式權力的一部分。第二,它不僅占了立法會的半邊天,而且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代表原則,根據基本法和8.31決定,未來行政長官普選時提名委員會也是按照功能代表原則組成。立法會最終目標是實現全部議員普選,功能代表制能與普選協調並存嗎?這是一個重大爭議。普選時按照功能代表原則組成的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是否具有正當性、合理性和排他性?後一個問題是占中者攻擊的靶子,照他們自己的理解,是導火索。
預計在2027之前還會鬧一次普選,最遲2037年之前如果還沒有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多半會發生比較大的危機。如何說服反對派接受8.31決定呢?他們是否會接受?焦點還將是提名委員會的權力與組成。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組成的原則性基礎與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原則一致,即便8.31決定原封不動地落實,如果立法會普選時取消了功能界別,那就表明香港社會拋棄了功能代表制的原則,對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民主正當性必將構成衝擊。此二者之間是唇齒相依的關係。
整體上,保留功能組別符合香港政道,但既然實現普選是憲定目標,就必須在功能組別的功利原則和普選的平等原則之間建立一個合適的關係。首先要確立優先次序,解決平等優先還是功利優先的難題。其次,要找到二者結合的邏輯關聯性和如何配比的度。
一、路徑依賴:基本法為什麼保留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功能代表制?
所有人談到香港的功能代表制時,不管是一般性介紹,還是持反對立場或者贊成立場的人,都會追溯到港英時期的立法局。
英國統治香港,為什麼沒有早些推行普選?如果那樣的話,回歸與否,怎樣回歸,就會與選舉聯繫在一起,甚至可能發生公投或者變相公投。這不是說可以阻止中國收回香港,因為香港沒有自決權,但回歸應該是“帶著民主回歸”,也就不存在回歸以後的普選之爭了,當然選舉過程的權力之爭就會更激烈,更加不確定。要不要代議制,要不要搞普選,英國人是盤算了利益做出選擇的。1992年換上彭定康加大步伐,也是利益考量的結果,只不過來不及了,由不得他了。
在白人占少數的殖民地,英國是不搞普選的,除非在撤退之前的某個階段把普選和民主作為未來的戰略部署。1976年英國政府遞交人權公約(ICCPR)批准書時,對於人權公約在香港適用特別是針對第25條B款作出了保留:“聯合王國政府就第二十五條B款可能要求在香港設立經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局,保留不實施該條文的權利。”直至香港回歸前,英國並未撤回對人權公約第25條B款的保留,保留繼續有效。嚴格地講,是英國欠了香港的民主債。
有人把港英統治模式概括為行政吸納政治,這話若不是一葉障目,就是有意文過飾非。難道除了行政就沒有政治了?月亮真的被狗吃了?政治在哪里?月亮掛在天上,香港政治在港督那裡!港英體制是個人獨裁制(autocracy)。為什麼人們一心求財無心問政?武力征服所致也。這才是最高的政治呢!說什麼行政吸納政治,政治早被槍桿子、炮筒子劃定了圈圈,華人被圈起來了。
至於老百姓生活,秩序主要不是靠行政,而是靠司法。司法化解社會矛盾,才是英國殖民統治的秘笈。在所有殖民地,政治和行政撤離了,普通法(和司法)就像命根子一樣留下了。香港今日司法照舊。
當我們看到香港從基本法起草一直到現在總有一股力量不停地要求普選時,我們是不是應該反問一句:為什麼在英國統治時期不鬧普選?這個問題不是賭氣的怨言,而是提醒人們思考,在什麼條件下,人們會產生民主衝動?在什麼條件下,人們可以提出普選訴求?
在英國統治下,英國人與華人是不平等的,是牧羊人與羊的關係。這不是港人的罪,是一個時代中華民族整體的悲劇。回歸意味著殖民者壽終正寢,港人可以當家作主了。回歸前,港人恐共,對社會主義制度不信任,這是回歸前最大的問題。因此,一國兩制是最合適的選擇。回歸以後,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是政治權威的建構。誰有權威?誰都沒有當然的權威。靠什麼建立權威?不能靠武力,也不能靠金錢,更不能靠世襲,只能靠港人的同意。選舉就是表示的制度,權威的難題就轉換成了採用什麼選舉制度的難題了。與英國150年的殖民統治相比,這是政道之變。
既然政道變了,為什麼要保留港英立法局實行的功能代表制,並且將功能代表制延伸到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上呢?為什麼香港不直接走“普選+政黨政治”的道路?在第45條和第68條起草過程中,各方觀點都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幾乎今天所有的說法在當時都出現了。具體的理由,這裏不重複。姬鵬飛把制度設計的思路總括為“既保持原有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言下之意是,因為行之有效,所以保持。
“行之有效”,確實是一個很好的理由,是路徑依賴的正當理由。路徑依賴是一種社會心態,一方面人們對舊制度產生了依賴的慣性,另一方面對於變革有恐懼感。路徑依賴,包括好的路徑和不好的路徑,“行之有效”的路徑,當然是條好路。其實,不僅政治制度如此,經濟、法律、社會制度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基本上原封不動。一國兩制建立在一個經驗性的假設之上,即:原有的那一套是“行之有效”的。效果如何衡量呢?最簡單的格式化的語言叫“繁榮穩定”。反過來,為了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最好的制度選擇就是保留原有制度基本不變。
香港原有制度真的行之有效嗎?換言之,香港的繁榮穩定在多大程度上與原有制度有正相關關係?是哪些制度保證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呢?回歸以後,哪些制度不得不變?哪些可以,哪些應該保留呢?這些問題是立法者應該考慮的基本問題。對於基本法已經選擇保留的制度,這裏我們不予置疑。但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那些保留的制度,在回歸以後是否還具有“行之有效”的條件?
那麼,就功能代表制而言,什麼叫行之有效呢?還是回到剛才引用的姬鵬飛講話的前一句,他將其效用概括為“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其實這等於肯定港英時期做到了這一點。如果我們看看1984年《白皮書:代議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1987年《綠皮書:一九八七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也會發現,港英當局認為功能代表制是合理的,但是需要進一步擴大代表性。
二、香港政道
牟宗三先生有一個兩分法叫政道與治道。他有一個斷言,“中國在以前於治道,已至於最高的自決境界,而政道則始終無進展。”道是道理、原理的意思,政道對應政權,治道對應治理。政道是政權形態背後的道理,治道是治理天下的道理,或者處理人間共同事務的道理,其本質是自上而下的。
借用牟先生的說法,我們提出一個問題:香港的根本問題究竟是政道問題還是治道問題?進一步說,香港應該奉行什麼政道才能改善治道?說得再明白一點,民主化能帶來好的治理嗎?
(一)香港的政治形態
什麼是香港回歸以後的政治形態?牟先生把國家政治形態(政權形態)分為封建規則政治、君主專制政治,以及立憲的民主政治。顯然,他沒有把社會主義國家納入考慮之中。所謂政權形態,包括國體和政體,西方一般統稱政體。按照一般教科書的定義,國體是指國家的性質,亦稱國家的階級本質。具體的說,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所處的地位。統治階級的性質決定著國家的性質。政體是指政權的組織形式。
香港是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對於地方一般不能談政權形態。但考慮到香港社會的構成具有自己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國家為香港專門制定了憲制性法律,賦予其一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因而不妨說它有一種政權形態。國體與政體分類的標準作為方法論,對於研究香港政權形態也是有益的,可以提供一些分析的框架,提出一些有意思的問題。
首先,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一國兩制最基本的事實依據,維持併發展資本主義也是一國兩制方針孜孜以求的方向。因此,當我們界定香港政治形態時,必須始終牢記這一點,自覺地將其與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區分開來。如果香港剔除資本主義,那麼,一國兩制就只剩下高度自治了,這個方針也就不適合了;如果香港剔除資本主義,甚至是否還需要或者值得享有高度自治,是應該存疑的。
其次,政體分類有很多標準,因此也有很多分類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權力和權威的來源,據此,國家可以分為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對於香港而言,權力來源於國家,因此,其政治形態的定性只能以權威的源泉為依據。權威來源於社會,選舉制度是體現權威源泉的具體形式。可是基本法對選舉制度採取了循序漸進的分期決斷,即首先實行混合選舉,最終實現普選。如此一來,香港的政道其實法定要發生改變。普選實現之日,也就是政道變化之時。在普選之前,香港的政治形態是地區代表制與功能代表制相結合的、均衡參與的選舉制。目前沒有一個名稱,我姑且稱之為混合代表制或雙軌代表制,也不妨稱之為混合民主或雙軌民主。
混合民主制,是民主制的一個變種,它的理論基礎是利益兼顧與人格平等兩項價值。利益或者功利這個商業社會的道德原則,與民主社會的人格平等,各有其政治代表制度,前者叫功能代表制,後者叫地域代表制,俗稱“數人頭”的代表制。
(二)香港政道與治道的關聯性
每一種政治形態都有正當化的理由,這大概就是牟宗三所謂的“政道”。如何論證香港的混合民主制呢?
請注意,上文引述的姬鵬飛關於基本法草案的報告把“利益”作為政治體制設計的原則,完整的說法是“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如何從利益過渡到政治代表呢?喬曉陽將其中的邏輯表達為“均衡參與”。其結構可圖示為:(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均衡參與。據信,通過均衡參與的選舉制度保障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喬曉陽特別指出,“沒有工商界,就沒有香港的資本主義;不能保持工商界的均衡參與,就不能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如此,完整的邏輯鏈條是:利益——均衡參與——資本主義。
“利益——均衡參與——資本主義”的格式可以分解為三個格式,如果我們將其中的“均衡參與”替換為“均衡代表”,可以表述為:
1、利益——資本主義。這個格式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本質,或者說道德原則。
2、利益——均衡代表。這個格式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一種關於政治代表的本質的觀念:利益代表;二是關於如何代表各階層利益的原則:均衡代表。這個格式表達的是政治制度與政道的關係。
3、均衡代表——資本主義。這裏的資本主義是均衡代表制度的目標,所以這個格式表達的是政治制度與治道的關係,即是說,無論選擇何種具體的治理方式,只有均衡代表的在政治制度才能維持和發展香港的資本主義。
上述三個格式合起來組成一個格式或者說一個邏輯鏈,均衡代表是中間項,是把另外兩個要素——利益、資本主義——聯結起來的要素。要論證“利益——均衡參與——資本主義”這個格式,就要分三步走。
這個邏輯是必然的嗎?換言之:(1)均衡參與的選舉制度,即普選與功能代表制混合的選舉制度可以最有效地保障香港社會各基層的利益嗎?(2)為什麼說單一的普選制不能有效地保障香港的資本主義?(3)選擇什麼樣的選舉制度,必須首先考慮哪些因素?經濟發展和各階層利益保護是政治制度的第一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嗎?(4)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麼,基本法為什麼還規定要以普選為最終目標?一旦實行普選,是否要排斥功能代表制?
也許不等我們直接從正面論述其中的道理,馬上就會遭到一種反駁:利益代表或者功能代表制起源於中世紀,在議會早期興起時是一個主導的,甚至唯一的代表原則。後來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逐步地走向了沒有特殊資格限制的普選,換了“政道”。現代世界歷史表明,自由民主與市場資本主義才是“天生配”。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香港究竟有什麼特殊性,必須保留功能代表制呢?
三、主張功能代表制的理由
功能代表制有國家層面的等級性選舉制度,也有社會層面的代表制,比如德意志帝國經濟會議,贊成和反對的理由既有交叉的一面也各有不同。這裡,我們只關心針對立法機關選舉的功能代表制。自俾斯麥承認普選之後,傳統等級制下的功能代表制在德國就已廢棄。當然,這不意味著此後再無人提出恢復或重新建構功能選舉制度的主張,更不意味著功能代表理論的死亡。
(一)規範的理由
1、社會的人:政治代表不可視而不見的深澗
職業代表制或功能代表制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從現實性出發,可以說,從一開始它就是一種社會理論的政治理論,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政治哲學。它的第一個命題就是:人是社會的人,公民僅僅是社會人的一個政治身份,是法律人為地創設出來的。
英文代表一詞拆開來就是“再現”,亦即使缺席者出場。民主政治代表制預設一個同一化的主體——人民;人民作為主權者是一個單一的主體。這是典型的法律擬制思維。由一個獨一無二的代表體——議會——來再現主權者人民,而在選舉產生這個代表機構的時候假定所有人都是同質的,因而可以採取數人頭的普選方式產生,也可以採取數人頭的方式做出決斷。普選制的一個致命的謬誤在於,當它把選舉權建立在自然權利的道德基礎上時,它在邏輯上從個體公民直接跳躍到了國家,而遺漏了社會這一環節,結果完全忽視了人的社會性和社會的異質性。全部個體被減約為一個個同一化的法律主體,即一系列基本權利義務的主體,叫做公民。韋伯說,選票的平等無非表示:在他社會生命的這個特定時間點,個人——帶有職業身份和家庭地位的個人,處於獨特的經濟或社會地位的個人——不見了,只剩一個公民。投票平等象徵了國家公民的和私域的敵對相反的政治統一性。
政治代表,代表的僅僅是“公民”,保障公民的政治平等,可是人是社會的人,是一個一個的功能行動者,有各種欲望和利益需要滿足。什麼是“政治”?政治代表可以代表人的各種利益嗎?可以代表那些支撐、建構、發展著社會的那諸多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功能嗎?換言之,如何把社會性附加到“公民”和“代表”的身上呢?
2、異質社會:政治代表的貧困
功能代表制的第二個命題是:社會是異質的,純粹的政治代表不能——至少不能充分地——再現異質社會。
如果社會是同質的,那麼,普選似乎沒有大礙。可是,一個同質的社會一定採行直接民主而不需要代表,因為同質社會是部落式的小社會,任何一個需要代表的大社會必然是異質的。即便民主的道德和法律減約與擬制是必要的,甚至可能具有某種真實性,可也無法否定人的社會性和社會的異質性。
異質性表現在多方面,最重要的兩點是勞動分化和階級分化。作為社會動物的個人,他是至少一項主要社會功能和諸多次要社會功能的載體和行動者。分工越細,社會子系統越發達,社會整體的功能就越完整和發達。現代社會是一個多種功能的複合體,各種功能的職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與此同時,社會分層也會越來越確定,階級衝突不可避免。普選的政治代表制面對兩極分化的社會格局奉行平等哲學,採取形而上學的方式拉平所有人,其正面的作用似乎可以概括為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然而,如何保障自由和社會的多樣性不至於遭受多數人暴政的侵害呢?如何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呢?普選的政治代表機構從邏輯上來說,不能“再現”社會功能分化和社會異質性,它的行為能力應當是極其有限的,局限於“政治”。
如果說在放任自由時代,因政治有嚴格的界限,代表是真實的話,那麼當代議會已經不得不大規模地介入經濟、社會領域,我們主要根據候選人的社會經濟政策選擇代表,這就違背了政治代表自身的邏輯限制。在理論上,政治代表不能代表任何經濟階級或集團,選民也應該從公民立場做出判斷,如此才能使議會代表公意。任何實證的觀察都會得出相反的結論,選民從自身利益、集團利益出發,政黨背後總是或遲或早站著各色的利益集團。根據抽象的政治代表概念,甚至連政黨存在的正當性都是可以質疑的。政黨不僅僅是開展選舉的機器,更是利益分化的結晶。
3、混合均衡憲法:民主不可分的謬誤
第三個命題是:社會是一個功能有機體,功能組織應該成為政治代表的(一類)選舉單元。
民主作為一種主權形式同樣具有絕對性,是一個“一”,不可分割。這種一元民主論受到兩個嚴重挑戰:一個來自聯邦主義,即縱向分割民主的主張;另一個是多元主義,它把國家視為眾多社會組織中的一種,或者叫一個等級。功能代表制理論分為兩支,一支結合了多元主義,主張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並行,走混合均衡憲法道路,另一支走向法西斯的法團主義。
社會是多種結盟的複合體,個人在社會中具有多種成員身份,而相應的組織是他們各種身份的保障。因此,真正的民主就當充分反映社會的多元性,讓各種功能組織都選出代表。一個完美的民主應該承認多種選舉單元,而不能僅僅限於公民個人。有人提出,民主至少要反映人的三或四個方面:作為一個商品或服務的生產者;作為消費者;作為公民,這也有兩個方面,一面是關心國防和國內秩序的公民,另一面是希望促進某種類型的文明的公民。
功能代表制理解的混合憲法,與傳統的混合憲法有很大區別,它指的是功能混合——根據社會功能結構來配置政治權力結構,以及社會均衡,即通過政治權力配置反過來引導社會均衡發展。
(二)實踐的理由
主張功能代表制的實際理由有三層:
第一、保證那些人數雖少但在社會中起主導作用的群體在選舉中保持相應的優勢。這是早期主張,意在維護特定等級特權。普選和政黨政治興起後,逐漸消失,在社會中的優勢等級轉而謀求通過政黨政治維護自身利益。
第二、比政黨更切合實際地代表人民利益。這是反對政黨政治的一種對策,黑格爾思想中有體現,俾斯麥時達到頂峰。
第三、吸納社會力量。把具有影響力的職業團體整合到國家中去,納入國家生活的正常軌道,最終促進國家機器良性運轉,而不應該任由其游離在國家之外,並經常成為和國家相對抗的力量。
其他民主國家的批評家主張功能代表制的動機是,他們厭惡現在的選舉制度和立法機關,希望為民主制發揮作用提供一個更為真實的基礎。具體而言,他們認為地域代表制有下述缺陷:
1、導致少數派的低代表,甚至完全不被代表;
2、頻繁出現事實性的少數派統治;
3、給那些“騎牆”投票人遠超比例的影響力並誘致腐敗;
4、政治鐘擺振幅太大;
5、強迫人們接受二流角色做我們的代表。
他們相信職業代表制具有下述優點:
1、相比地域代表制,建立在更重要的利益的基礎上。工作時間是清醒的白天,人們靠工作養家糊口,同事關係要緊。居家是休閒時間,鄰里關係淡漠。
2、選民更充分瞭解候選人。同業者易於瞭解候選人,更嚴格判斷其能力,可以產生專家議會。
3、可防止目前立法職位被少數小職業壟斷的局面。一個職業的人不清楚別的行業的狀況和問題,他的利益也與居住同區的其他職業的人不同,不能指望他能代表別行業的利益參與立法,而行業代表者與選民利益天然一致,而且同行有天然感情,就像鄰里有天然感情一樣。
四、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
對於香港政道,核心的觀念是利益原則或功利原則。要理解香港政道,一定要借助商業社會的理論。商業社會(commercial society)的概念一直被我們當作政治日常用語,沒有得到嚴肅的理論闡釋。
商業社交性(commercial sociability)是一種習得社交性,商業社會的原則是功利(utility),相比於政治結盟(union)屬於低位的、次級的和諧(concord)。政治結盟起源於承認的需要(need of recognition),而不是生理需要(need)。承認的需要也就是霍布斯說的傲慢(pride),即希望別人承認自己卓越。除非嚴格平等,否則承認的需要便是個零和遊戲,結果只有贏家和輸家。正因為如此,只有結盟才能整體地自我保存。這才是政治的起源。商業社交性可以令大家互贏,它的結果是一個富裕的和諧社會,但這個社會如果沒有政治也是沒有根本安全的,因為商業社交性或者功利考慮無法真正徹底克服承認的需要,也無法防禦敵人,因此是低位的次級的和諧。這一點,從猶太人的歷史命運看的最清楚。
功利與傲慢始終處於對抗和緊張之中。從古羅馬到中世紀,共和國的概念與美德聯繫在一起,排斥商業,認為商業會腐化政治。新教倫理賦予勞動以道德價值,商業美德才成為了共和國的主流價值。蘇格蘭啟蒙運動產生了重商主義,把商業秩序視為國家建構的基礎,把富強作為國家的目標。孟德斯鳩認為,自愛與商業的結合是現代歐洲君主國家維持社會和經濟活力的穩定要素。發展到今天,多數的共和國也是商業國,兩種道德原則並存。普選基於公民資格,即平等原則,而非利益。特殊群體的利益怎麼辦?資本主義國家通常採取兩個辦法。一是自由憲政主義,用以保障基本權利和自由,特別是私有財產權和政治自由。二是政黨和壓力集團,用以影響政策和立法。可以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選與資本主義確實存在矛盾,普選是資本主義的解毒劑。普選與私有財產權相互博弈,也相互勾連,實現社會的平衡。
為什麼功利原則對於香港政道特別重要?首先,香港不是一個主權實體,而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區域。當我們談論香港政治形態時,不要忘記,一個非主權單元與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的主權國家相比而言,在政治制度的選擇上缺少一些重要的因素,同時又附加了一些重要因素。缺失因素中最關鍵的是制憲權,其中包括政治制度決定權。附加因素中最關鍵的是國家層面社會主義的制度環境,在社會主義的汪洋大海中維持一個穩定繁榮的資本主義小島,維持一個國際大都市,究竟需要何種政治制度,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其次,中國近代以來憲法精神演進的路徑是從富強到自由。現在的目標還是富強,中國夢即偉大復興之夢。在現代共和國的建構進程中,香港加入晚了,但正趕上國家改革開放,即開始實行重商主義。基本法對於香港的定位極為明確,就是維持一個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香港治理的目標是繁榮穩定,繁榮當然指向商業社會。基本法對於港人沒有提出古典共和國的美德要求,比如無私、比如戰士形象。港人不向國家交稅,也不服兵役,沒有軍事能力也無權擁有軍隊。理解香港政治形態,必須從國家對香港的政治期待、政治定位出發。香港畢竟是國家的一個行政區域,不能有意無意地把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來想像,而應該把它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來想像。
五、尋找平衡點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過於政治化不僅背離立法者的初心,也對香港不利,因為香港一旦沒有了繁榮的商業,也就失去了魅力,不僅港人幸福指數會下降,而且連自治的根基也會動搖。
然而,香港首先是一個社會。社會中的人天然地有承認的需要。現代社會承認需要難題的解決之道是平等,即平等地承認。基本法也是奉行這個道。利益(功利)與平等的關係在香港社會似乎比那裡都緊張,此為香港政道的內在張力。香港的問題既非要否定商業社會的道德基礎,也非要否定民主的道德基礎,而是要找到一個度,一個平衡點。
我們在思考未來的普選制度時,不能僅僅局限於政道之變,而要從治道反過來思考政道。善治的政體才是好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