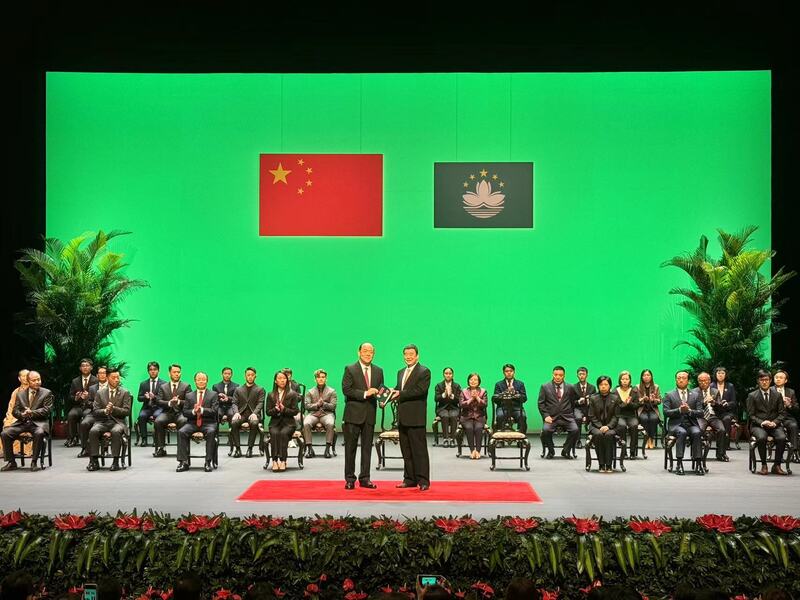依憲治國是一個國家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這是清末以來有識之士的普遍共識。[1]筆者認為,《澳門基本法》作為全國人大制定的、在澳門特區實施的憲制性文件,也同樣是澳門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它之所以能擔起此項重任,正是因為它包含了現代憲制性文件所應包含的國家統一與地方自治有機結合、民主、法治、權利等基本價值。[2]我們應當珍視基本法確立的這些基本價值,並在基本法的實施中時刻保護它們。
一、國家統一與地方自治的結合
首先,我們來梳理一下國家統一與地方自治的結合對於澳門持續發展的意義。根據《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3]在外交和國防之外的事務上,澳門特區自行行使立法權、行政管理權和司法權;[4]除憲法、基本法和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外,其他全國性法律不在澳門特區實施;[5]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收入全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支配,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6]所有這些,都是基本法賦予澳門高度自治權的體現。
那麼,高度自治權對於澳門的發展來說具有何種意義呢?基本法制定以及澳門回歸祖國之初,高度自治當然具有使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的功能。但是,高度自治的意義並不止於此,它對於澳門回歸之後的良好發展意義重大。
第一,它能提高澳門治理的效率。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傑佛瑞·斯通教授在論證地方自治的價值時說過,“考慮到在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對特定問題在不同地區採取不同的解決方案也許是個恰當的做法”。[7]這個道理其實是比較明顯的,也就是說,由於一個國家不同地區往往面臨不同的問題需要處理,地方自治所固有的因地制宜的特性,將提高地方治理的效率,避免全國一刀切的弊病。近代以來,澳門長期在葡萄牙的管制之下,在居民生活方式、經濟發展水平、政府治理效率、法治化程度等方面形成了與中國的其他地區有很大不同的特點,所面臨的問題也與中國的其他地區不同。因此,行使中央賦予的高度自治權,因地制宜,延續原有的法律制度,制定針對本澳社會問題的規則,無疑能夠提高澳門的治理效率。
第二,它能使本澳政府和居民保持敏銳,並能促進本澳民主的發展。高度自治還不同於普通的地方自治,其“高度”既體現于自治範圍之大,而且體現在除憲法和少數全國性法律外,絕大多數全國性法律不在澳門實施。這種自治會使澳門政府和居民產生“自己的問題必須自己解決”的責無旁貸的意識和心理,不能依靠更高層級的共同體意志和政府政策。在此狀態下,本澳政府和居民必須保持對本澳社會問題的敏銳,把自己的問題解決好。同時,澳門特區政府作為一個國家的地方政府,與居民距離近,加上澳門面積不大,人口絕對數量不多,居民會感覺自己的參與會直接影響政府的決策,自己的遲鈍會導致政府的決策偏離公共利益。這樣一來,澳門居民就會成為“經典民主理論所珍視的積極公民,而不是遙遠的中央政府的被動客體”[8]。這將使澳門的治理形成良性循環,能夠使澳門的各領域立法保持基本公正。
另一方面,國家統一也是體現在《基本法》中的“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基本法》第一條明確宣示,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因此,澳門雖然是一個具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個統一國家的組成部份。國家統一絕不應當僅僅是名義上的統一,它必須在很多方面具有實質的統一特徵,例如市場要統一,商品可以自由流通,人口構成一個自由流動的共同體,道路可供國民平等使用,就業機會由國民平等分享,共同承擔國防費用等等,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在財政上還要沉浮與共。
為什麽一個統一的國家需要具備這些實質特徵?最根本的目的無非是保障國民的自由和最低生存保障。一個大國的優勢就在於不經其他國家的同意,國民即可在廣闊的土地上自由遷徙,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工作,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氣候和自然風景,讓自己的才能和人格得到自由發展,客觀上也同時使一個國家生氣十足。而當一個地區面臨意外的自然災害或地質災害時,整個國家的國民將與他們沉浮與共,在居住區域、工作機會等方面和他們平等分享。
雖然澳門回歸以後,在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經濟差距等很多方面與內地存在很大不同,為了社會秩序的穩定需要保持高度自治,但是長期來看,澳門需要與中國其他地區一起分享統一大國的好處,在國土分享、工作機會、市場機會甚至藝術靈感的激發等方面充分利用統一大國的資源。目前,中央政府支持、澳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是澳門利用統一國家優勢的絕佳契機。事實上,澳門不僅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部分,當然也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澳門今後的持續健康發展還有更大的資源可以利用。
二、民主
《基本法》所包含的第二個基本價值是民主。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為澳門確立了民主政治體制。《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澳門立法會又於2009年制定了《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規定絕大多數基本法律和重要法律由立法會制定,並且規定,法律優於其他所有的內部規範性文件,即使該等文件的生效後於法律。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也是由各界別人士組成的400人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這些制度使澳門的社會治理具備了基本的民主因素。
在此民主政治體制之下,自澳門回歸以來,澳門立法會通過審慎的討論程序,制定了大量法律,對澳門社會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作出了規範。例如,澳門回歸伊始,澳門立法會制定了《審計署組織法》、《司法官通則》、《司法組織綱要法》、《政府組織綱要法》等重要法律,今年又剛剛修改了《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和《司法組織綱要法》,並制定了《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和《輕型出租汽車客運法律制度》。在制定這些法律的過程中,立法會都進行了較為審慎的辯論,並對辯論過程進行了電視直播。
除了立法職權以外,立法會還有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的權力和責任。去年下半年,立法會就一些民眾關注的重大問題進行了辯論,例如,輕軌的建設與投資問題多次成為立法會辯論的主題。
民主是一個共同體持續健康發展的必備制度,這一點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一個人的知識和智慧是有限的,對社會問題的瞭解和認識往往不全面,而民主則能借助民眾和民意代表的知識和智慧,做出更加理性的決策。而且,由於民主制度能夠讓各種聲音獲得自由表達,而在這種自由中錯誤的觀點往往能夠得到糾正,尤其是長期來看,正確的觀點往往能夠勝出。此外,民主制度下,民意機構通常具有對行政機構的政治監督權,通過財政監督、重大事項的調查與質詢以及人事控制,能夠使行政機構的行為基本符合公共利益。
目前,澳門立法會在制定重要法律、就重大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和決定等方面已經充分發揮了民意機構的作用,在控制政府的財政預算方面也已經發揮了一定作用。這些都是《基本法》確定的民主政治體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得以貫徹實的表現,對於澳門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我們必須珍惜民主這一基本價值。當然,目前民主制度還在澳門繼續發展,我們應該立足於澳門的實際社情、民情,謹慎推動這一進程,使民主這一價值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法治
一個地區的法治狀況主要體現在政府權力受到約束的程度、腐敗得到控制的程度、基本權利得到保護的程度、民事和刑事司法的公正程度等方面,而關鍵的制度指標則是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實現程度和政府不同分支之間分權制衡的程度。
《基本法》為此作了明確規定。《基本法》第八十三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干涉;第八十九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官依法進行審判,不聽從任何命令或指示。法官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這些都是對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規定。《基本法》還對法官的職位提供了保障,第八十七條第二款和第三款規定,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其職責或行為與其所任職務不相稱的情況下,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院長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終審法院法官的免職由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審議委員會的建議決定。這就避免了法官存在可以被任意免職的顧慮。《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七)項還規定了立法會在行政長官在嚴重違法或瀆職但不辭職時的彈劾權。這種分權制衡同樣是確保澳門法治不被破壞的重要規定。
法治的直接目的當然是保證符合民意和公共利益的法律得到最大程度的遵守,從而保證個案公正,保護民眾的權利不受他人和政府的侵犯,使民眾生活在安全和可預期的狀態之下。但是,我們不難發現,法治的這種直接作用對於一個共同體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直接保障作用。只有對自己的權利受到保護有信心,民眾才有“恒心”,為自己的安居和創業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外來投資者也才有“信心”,可以長遠打算自己的創業計畫,可以在合法的情況下簽訂重要合同,也敢將自己的大量資產用於大規模工程的建設。澳門過去的良性發展正是得益於澳門法治化程度之高,今後的良性發展同樣離不開對法治的堅持。
當然,筆者認為目前法官職位的穩定性與其他法治發達國家或地區相比仍然有待加強。[9]三名法官組成的審議庭可以建議罷免一名法官,可能無法充分防止行政權力對法官職位的任意干預;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審議委員會可以建議罷免終審法院的法官,沒有規定需要多少名議員的支持,如果僅僅過半數即可提出罷免建議,不僅無法充分防止建議的任意性,而且使法官在考慮少數人的基本權利是否受到侵犯時不能不顧慮多數民眾的意見,無法對基本權利提供充分的保護。
四、權利和自由
最後,《基本法》還包含權利和自由這一基本價值。《基本法》第三章列舉了居民的基本權利,包括平等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名譽權和隱私權、遷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選擇職業和工作的自由等等。
有些權利主要與個人的私人生活和個人尊嚴有關,如人身自由、名譽權和隱私權、宗教信仰自由、婚姻自由等,這些權利通常與公共秩序和政治、經濟在整體上的發展沒有直接關係,而有些權利則直接與一個共同體的經濟、政治、公共道德的發展有直接的密切關係。例如,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如果能夠得到無障礙行使,民眾的意見就能對政府的行為形成直接控制,政府的立法和執法行為通常不會偏離公共利益,就不會受到某些壟斷的利益集團的長期俘獲,有助於公平競爭環境的維持,這對於一個共同體經濟的發展無疑是有利的。再如,言論自由如果能得到充分保護,不僅可以保證民主選舉的理性程度,而且還可以借助日常的資訊交流和輿論監督,避免一些不合理政策的存在和產生。這也同樣有助於消除澳門持續健康發展的制度障礙。
《基本法》保障的選擇職業和工作的自由更與澳門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職業和工作對個人來說是謀生的手段,但是對與整個社會來說,就是一個人貢獻自己的才智、促進社會發展的途徑,整個社會的發展不正是每個人借助自己的職業創造的成果的疊加嗎?這項自由意味著政府不能通過不平等、不合理的規則限制本來有資格從事某項職業的權利,否則一個人的才能就無法得到充分的施展,而一個人在成年之後,因興趣、學習經歷等原因,往往具備某一方面的特長和技能,不具備其他方面的技能,因此,他選擇職業的餘地並不是很大。如果選擇職業的自由受到不合理限制,這不僅嚴重影響一個人謀生的能力,而且嚴重妨礙他利用其本來就有限的途徑為社會做出貢獻。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藥劑師執照案”中擲地有聲地指出,選擇職業的自由只能為了迫切的公共利益而受到限制,而且對公共利益的這種保護的實現,不能夠通過對選擇自由的影響更小的限制來達到。在對職業選擇自由之侵犯不可避免的情形下,立法者必須永遠使用對基本權利限制最小的調控手段。[10]事實上,澳門立法會剛剛制定的《輕型出租汽車客運法律制度》規定的“只有資本不少於澳門幣五百萬元公司方可參與準照的公開競投”[11]就引發了很多人的質疑:如果說出於賠償責任能力的考慮才限制競投準照的條件,那麼在保險業如此發達的現代社會,實在沒有必要將競投準照的條件限制在資本不少於五百萬的公司;這項限制將剝奪有熟練駕駛技術且有能力支付保險費的人從事出租車營運的權利。由於截止目前還沒有聽到對此更有說服力的辯駁,筆者認為這種質疑不是毫無道理的。
事實上,即便是只與個人的私人生活和個人尊嚴有關的權利,對於一個社會的發展也至關重要。隱私、宗教信仰、婚姻是一個人的基本尊嚴和基本信仰,如果受到不當侵犯,人們會產生痛苦和不公正感。如果整個社會的基本公正無法得到保證,人們的怨憤就會增多,公共道德感就會下降,每個人都變成自保、自利的極度利己主義者,寬容與合作的社會氛圍將無法維持,整個社會就會處於時刻爆發大大小小的沖突的狀態,甚至整個社會的民主自由秩序也因寬容與合作文化的消失而處於危險之中。這種狀態如何保證一個社會的良性持續發展呢?
還需要注意的是,權利和自由有限制多數人決定的意義。民主加法治能夠保障多數人的利益,但是多數人的決定未必能保護所有人的利益。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雖然多數決定通常與權利和自由並不沖突,而且是權利與自由的重要保障,但是有時多數人可能做出侵犯少數人基本權利的決定,這也正是各國憲法規定權利條款並確立憲法審查制度的主要考慮之一。事實上,在澳門,防止多數意見影響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的意義尤其重大,因為澳門是一個面積和人口規模不大的社會,容易形成固定的多數意見,少數意見很難勝出,而且這種格局往往長期恒定。麥迪遜曾經不無道理地指出:“社會越小,特殊黨派和利益集團的數量就越少;不同黨派和利益團體的數量越少,相同黨派形成多數的機遇就越頻繁。況且形成多數的個體人數越少,其範圍越狹窄,他們協作並實現壓制計劃就越容易。”而在一個更大範圍的人口共同體中,“你將帶入更多樣化的黨派和利益集團,你將減少全體的多數具備同樣動機去侵犯其他公民權利的可能性”。[12]因此,在澳門,我們越應該警惕長期、恒定的多數意見,越應該保護言論自由和其他基本權利,在涉及基本權利的問題上,我們需要保持開放和寬容的心理,傾聽分散的少數人的聲音。在具體的法律程序上,我們就需要加強法院對基本權利的保護,正是因此,我們需要加強法官職位的穩定性,尤其不能輕易受到立法會簡單多數意見的左右,應該在立法會審議程序和難度上設置更高的門檻。
結語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授權之下,全國人大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將“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落實到法律文件,在“一國”的大前提下,賦予澳門特區高度自治權,並為澳門確立了民主與法治的政府結構,宣示了需要保護的居民基本權利。這些人類最先進的政治文明價值不僅確保了澳門回歸以後的社會穩定,而且為澳門的長期健康發展奠定了憲制基礎。在紀念《澳門基本法》頒布26周年的研討會上,細數這些基本價值,並思考它們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的關係,是很有意義的。
註釋︰
[1] 參見張千帆:《憲法學講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109-148頁;又見荊知仁:《中國立憲史》,臺灣聯經出版社1984年版。
[2] 參見張千帆:《憲法學講義》,第49-54頁。
[3] 參見《澳門基本法》第二條。
[4] 參見《澳門基本法》第十三、十四、十六至十九條。
[5] 《澳門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
[6] 《澳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7] [美]杰弗里·斯通:《联邦主义的价值以及实现它们的一些方法》,程迈译,载张千帆、[美]葛维宝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译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7页。
[8] 同上注,第11頁。
[9] 《澳門基本法》第八十七條第二款和第三款規定,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其職責或行為與其所任職務不相稱的情況下,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院長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終審法院法官的免職由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審議委員會的建議決定。
[10] Apothecary Act Case, 7 BVerfGE 377;转引自张千帆:《法国与德国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315页。
[11] 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2019號法律《輕型出租車客運法律制度》第五條。
[12]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Clinton Rossiter (ed.), NAL Penguin (1961), p. 83. 此處譯文引自張千帆:《憲法學導論》,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三版,第220頁。